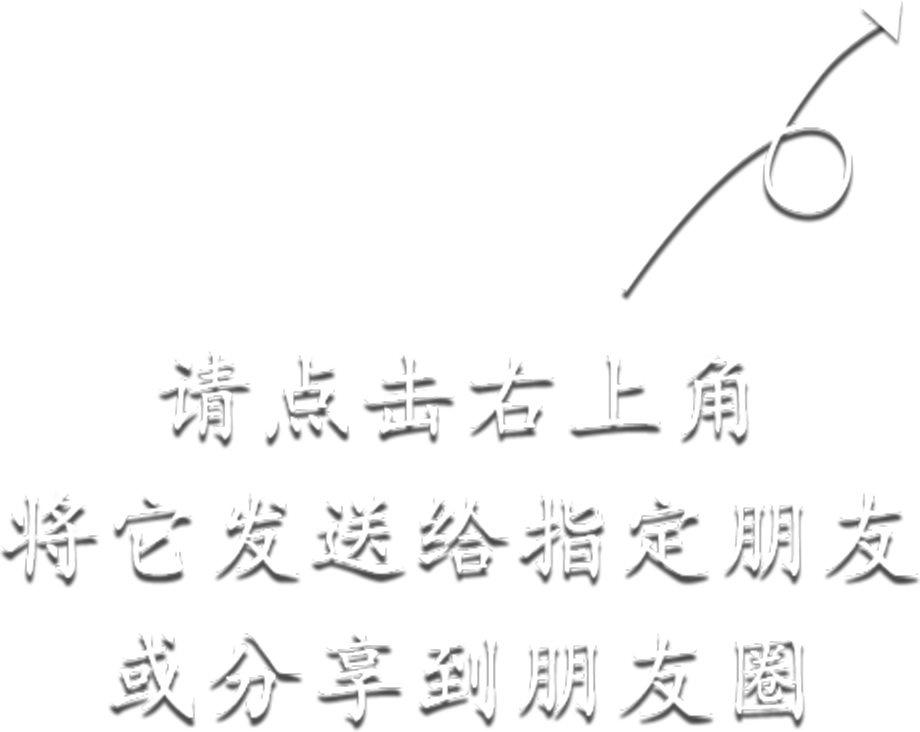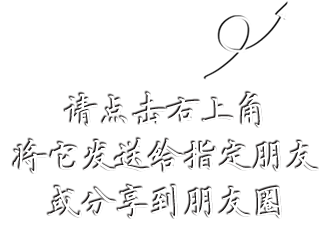□王梅
妈妈28岁生下我,那一年,她的母亲74岁。
记忆里的外婆一直拄着一根拐棍儿,总是笑嘻嘻的,她的笑容里带着清澈而简单的欢喜,口里右下方那颗左右无邻的牙在她的笑容里更添喜感。
村尾丁字路口有棵大皂角树,树迎着村口的那一面,呈半环形摆放着一些石凳。附近村民闲时都喜欢去那儿坐着,大家并不约叫,去时有人便老远就开始或打招呼、或调侃,没人就一人坐着。尤其是晚饭时段,总有三三两两的村民端着饭聚在树下,没有石凳坐了就蹲在地上,有的人饭吃完了把空碗放在脚边接着“喷”,直到大家散伙才回家。外婆喜欢坐在那棵皂角树下正对着村口的那块大石板上,妈妈领着我和妹妹来的时候,她就是在等我们,走的时候就是在送我们。
外婆的家住在“丁”字的左肩中间,离路口二三十米,那时没有电话,估莫着我们要来的前几天开始,她一上午都会从家到树下来回好几次,将短暂的希望和失望交替到正午。每次从外婆家离开的时候,妈妈都是推着自行车走出村口才带上我们骑行,我通常边走边回头看外婆是否还坐在那儿,每次都会在“丁”字的脚后跟处踮着脚伸着脖子再认真看一次,村子的主路很长,最后看到的都是一团灰和一点白:灰色是外婆的大襟袄,她的袄都是一个样式,有的洗得发白,远处看就是浅灰色;白色是她的头发,白得泛银光,是“满头银发”最生动的呈现。每次我都会在最后一次回望时定定站几秒,我要在心里确认好那团淡水墨般的灰和白就是外婆,才会满足地转身跟妈妈回家。
我没有见过外婆穿过现代的或是对襟儿的衣服,都是灰蓝色系的中长偏襟儿样式,底下是黑色大裆裤搭配同色或灰色裹腿布,外婆的裹腿布通常缠裹在脚脖子至小腿肚处,再往下是一双小脚。家住中原农村的外婆出生在1903年,清政府颁布禁止缠足令的时候,外婆已经被缠足。“那时脚掌心已经凹得能穿过红蜀黍(高粱)秆。”外婆摸了摸脚底板说。
那是一个夏夜,还是个孩童的我和外婆睡在一张床上,我看到她的脚和我们都不一样,脚面弓起,脚底板前后的肉在中间挤出个1到2厘米深的缝儿,脚趾头除了大拇指,全都卷压在脚心,尤其是小拇指,连着脚掌都被卷过去了,像是被掀折的书页。我很是好奇,也有点害怕,想摸一摸,又担心她会疼。我用一根手指头轻轻抠她的脚趾,试图把它们掰平回来。那一夜,睡着以前,我们都在聊她的小脚。
外婆说脚裹尖的时候,家里大人就让她多下地干活,自己多踩踩,她疼得整夜睡不着,白天还得干活。我问她,你为什么不反抗?你爸妈不心疼你吗?为啥还要让你干活?你不会不干吗?……外婆说咋会不心疼?
在我的记忆里,外婆的窑洞冬暖夏凉,那个夏夜躺在外婆身边,空气凉丝丝的,盖着晒过的小薄被,闻着太阳的味道。我舒服得困意频袭,把外婆的话都截成了片段:“刚缠好用脚后跟踮着走,走一步痛一下……坐下时是一阵阵抽痛,睡觉时也会又胀又痛……”我睡在外婆身边,深深的好奇和认真的问话像时光回馈给外婆的宠爱,外婆舍不得睡,细细地回答着我的问题。我记得外婆每回答我一个问题最后都笑着说“那也没办法呀”。她从没有抱怨过父母,也没有抱怨过生活。
外公我没见过,妈妈还没出嫁时他就过世了。听妈妈说她家建设新院子的时候,外公心劲儿可大了,天不亮就自己起来“码窑顶”,一丝不苟,同村所有窑顶都没他家的美观。新院子有五个窑洞,后来舅舅又建了两间楼板房,墙体是泥坯和红砖。舅舅脾气不好,但我也从没听外婆抱怨过舅舅或命运。有时我会想,外婆也许是“无感”之人,但她的笑又那么通透。外婆始终住在离大门口最近的一个窑洞里,里面黑乎乎的,却给了我“冬暖夏凉”最真实的感受。我和妈妈每次去看外婆,都住在那里。
记得小时候妈妈带我们去外婆家,一般都是买些点心带着,偶尔也会有罐头。到了外婆家,那些点心会被她第一时间打开,分给我和妹妹吃,有时候她也会和我们一起吃,高兴得合不拢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亲戚们之间的探望,一般就只在过端午节和中秋节的时候,晚辈去看长辈;带的礼物除了应景的粽子或月饼之外,也会搭配一兜点心。通常,那些点心和月饼外婆都舍不得吃,藏起来等我们去的时候给我和妹妹吃。印象里这些点心只有一小部分在保质期内等到了我和妹妹,剩下的在变质初期被发现后,外婆会把它们转移到悬在窑顶中间的篮子里通风保存,并开始吃它们。
有一次,妈妈一个人去看外婆,回来的时候给我和妹妹带了已经生出一两个霉点的月饼,妈妈也是个节俭的人,那一次,妈妈想着拿回来把霉点抠掉她自己吃,谁知被爸爸先发现了,还告诉了奶奶。奶奶很生气,站在院子里冲着我妈讽刺我外婆:“没东西给孩子可以不给,把坏了的点心拿回来给孩子吃,吃坏了算谁的……”现在想来,很是心酸。奶奶很疼爱我们,但生长、生活在县城的她不能理解外婆的行为。把好东西收拾起来留给小女儿的孩子吃,是外婆的执念啊!
关于这些,传到外婆耳朵里时她也不生气,笑着说:“你奶奶这个老鳖一。”当我们问什么是“老鳖一”时,她就笑得不能自已,眼泪都笑出来了。
外婆的笑容是被岁月淬炼过的满足、珍惜、喜悦,为数不多的牙齿在她的笑容里显得格外可爱。她定格在我记忆里的还有她的白发,每一根发丝都像披着阳光在微风中轻舞的精灵,有种让人想触摸的吸引力。
我上大二的时候外婆去世了,97岁,一生无大病,没进过医院。妈妈给我打电话时很伤心,我心里很疼,生理性的,但我又无话可说,极力去体会着妈妈描述的外婆的最后时光。外婆没享过什么福,这让我一直到现在都很难受,尤其在我吃着美食的时候,常会想到“如果外婆在”。之后,我梦见过一次外婆,她在邙山山脉上飞舞,满面笑容,像神仙又像精灵,自由自在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