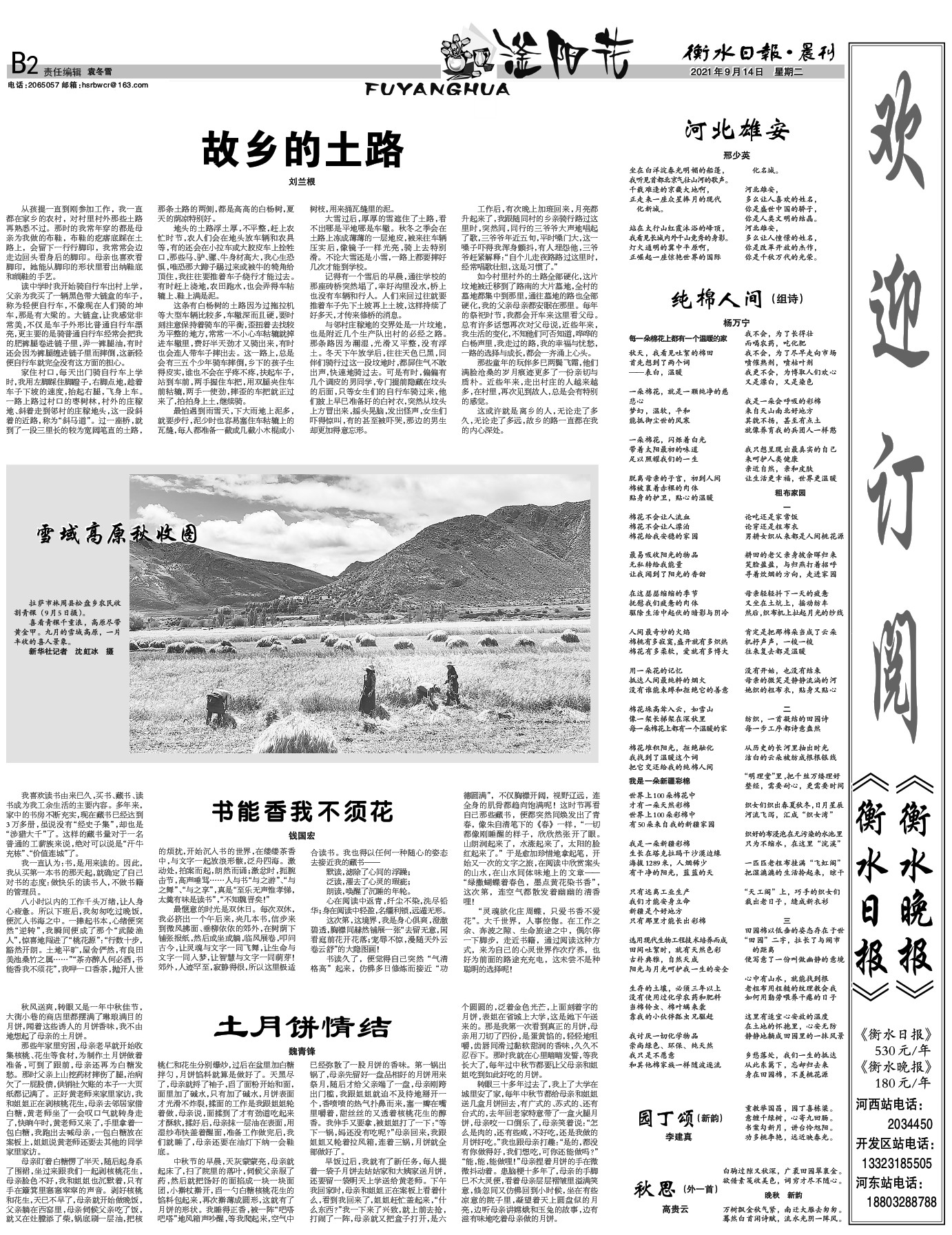- 放大
- 缩小
- 默认
故乡的土路
刘兰根
从孩提一直到刚参加工作,我一直都在家乡的农村,对村里村外那些土路再熟悉不过。那时的我常年穿的都是母亲为我做的布鞋,布鞋的疙瘩底踩在土路上,会留下一行行脚印,我常常会边走边回头看身后的脚印。母亲也喜欢看脚印,她能从脚印的形状里看出纳鞋底和绱鞋的手艺。
读中学时我开始骑自行车出村上学,父亲为我买了一辆黑色带大链盒的车子,称为轻便自行车,不像现在人们骑的坤车,那是有大梁的。大链盒,让我感觉非常美,不仅是车子外形比普通自行车漂亮,更主要的是骑普通自行车经常会把我的肥裤腿卷进链子里,弄一裤腿油,有时还会因为裤腿缠进链子里而摔倒,这新轻便自行车就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担心。
家住村口,每天出门骑自行车上学时,我用左脚踩住脚蹬子,右脚点地,趁着车子下坡的速度,抬起右腿,飞身上车。一路上路过村口的枣树林,村外的庄稼地、斜着走到邻村的庄稼地头,这一段斜着的近路,称为“斜马道”。过一座桥,就到了一段三里长的较为宽阔笔直的土路,那条土路的两侧,都是高高的白杨树,夏天的荫凉特别好。
地头的土路浮土厚,不平整,赶上农忙时节,农人们会在地头放车辆和农具等,有的还会在小拉车或大胶皮车上拴牲口,那些马、驴、骡、牛身材高大,我心生恐惧,唯恐那大蹄子踢过来或被牛的犄角给顶住,我往往要推着车子绕行才能过去。有时赶上浇地,农田跑水,也会弄得车轱辘上、鞋上满是泥。
这条有白杨树的土路因为过拖拉机等大型车辆比较多,车辙深而且硬,要时刻注意保持着骑车的平衡,歪扭着去找较为平整的地方,常常一不小心车轱辘就掉进车辙里,费好半天劲才又骑出来,有时也会连人带车子摔出去。这一路上,总是会有三五个少年骑车摔倒,乡下的孩子生得皮实,谁也不会在乎疼不疼,扶起车子,站到车前,两手握住车把,用双腿夹住车前轱辘,两手一使劲,摔歪的车把就正过来了,拍拍身上土,继续骑。
最怕遇到雨雪天,下大雨地上泥多,就要步行,泥少时也容易塞住车轱辘上的瓦缝,每人都准备一截或几截小木棍或小树枝,用来捅瓦缝里的泥。
大雪过后,厚厚的雪遮住了土路,看不出哪是平地哪是车辙。秋冬之季会在土路上冻成薄薄的一层地皮,被来往车辆压实后,像镜子一样光亮,骑上去特别滑。不论大雪还是小雪,一路上都要摔好几次才能到学校。
记得有一个雪后的早晨,通往学校的那座砖桥突然塌了,幸好沟里没水,桥上也没有车辆和行人。人们来回过往就要推着车子先下土坡再上土坡,这样持续了好多天,才传来修桥的消息。
与邻村庄稼地的交界处是一片坟地,也是附近几个生产队出村的必经之路。那条路因为潮湿,光滑又平整,没有浮土。冬天下午放学后,往往天色已黑,同伴们骑行过这一段坟地时,都屏住气不敢出声,快速地骑过去。可是有时,偏偏有几个调皮的男同学,专门提前隐藏在坟头的后面,只等女生们的自行车骑过来,他们披上早已准备好的白衬衣,突然从坟头上方冒出来,摇头晃脑,发出怪声,女生们吓得惊叫,有的甚至被吓哭,那边的男生却更加得意忘形。
工作后,有次晚上加班回来,月亮都升起来了,我跟随同村的乡亲骑行路过这里时,突然间,同行的三爷爷大声地唱起了歌,三爷爷年近五旬,平时嗓门大,这一嗓子吓得我浑身颤抖,有人埋怨他,三爷爷赶紧解释:“自个儿走夜路路过这里时,经常唱歌壮胆,这是习惯了。”
如今村里村外的土路全部硬化,这片坟地被迁移到了路南的大片墓地,全村的墓地都集中到那里,通往墓地的路也全部硬化,我的父亲母亲都安眠在那里。每年的祭祀时节,我都会开车来这里看父母。总有许多话想再次对父母说,近些年来,我生活的变化,不知他们可否知道,哗哗的白杨声里,我走过的路,我的幸福与忧愁,一路的选择与成长,都会一齐涌上心头。
那些童年的玩伴多已两鬓飞霜,他们满脸沧桑的岁月痕迹更多了一份亲切与质朴。近些年来,走出村庄的人越来越多,在村里,再次见到故人,总是会有特别的感觉。
这或许就是离乡的人,无论走了多久,无论走了多远,故乡的路一直都在我的内心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