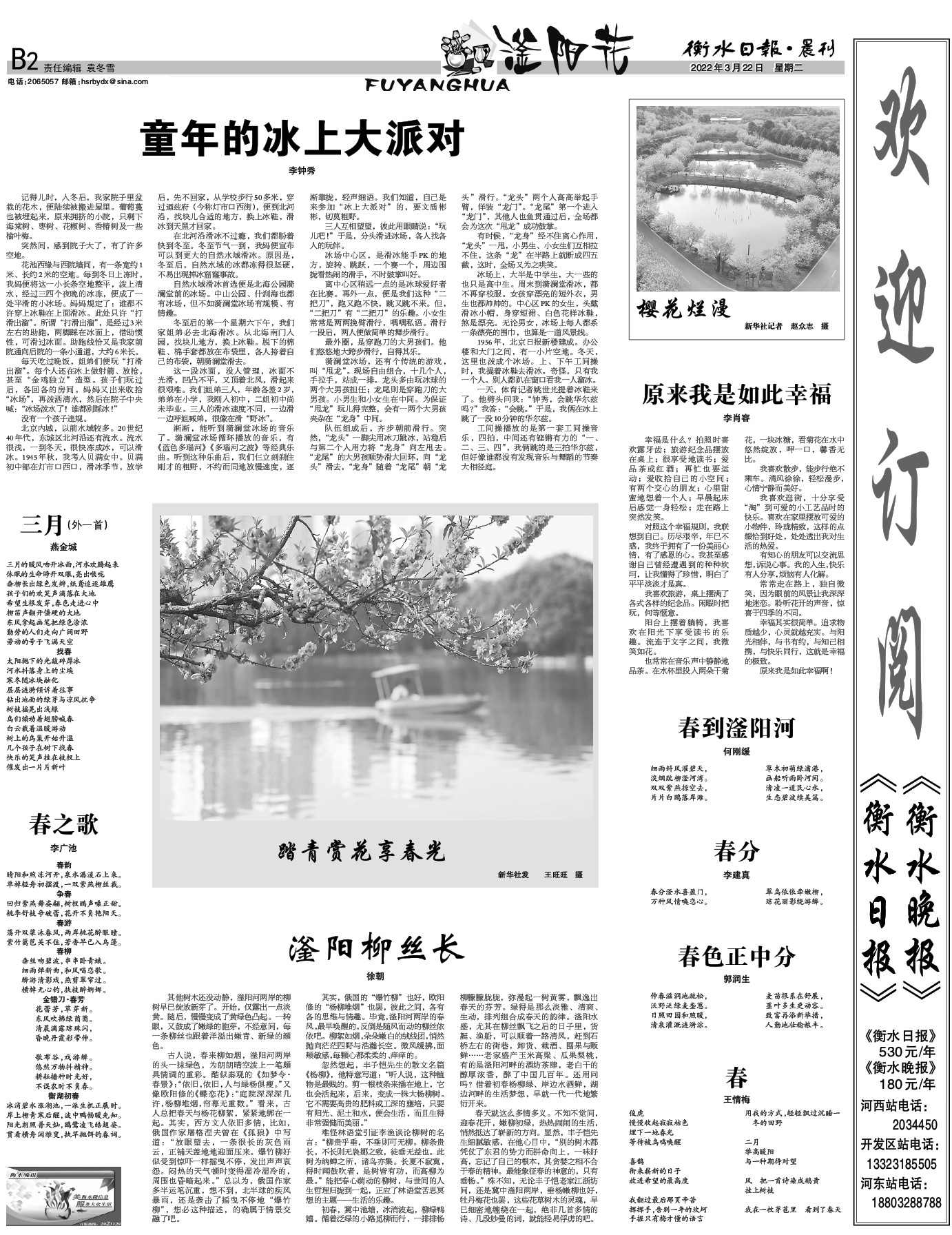滏阳柳丝长
徐朝
其他树木还没动静,滏阳河两岸的柳树早已绽放新芽了。开始,仅露出一点淡黄。随后,慢慢变成了黄绿色凸起。一转眼,又鼓成了嫩绿的胞芽,不经意间,每一条柳丝也跟着洋溢出嫩青、新绿的颜色。
古人说,春来柳如烟,滏阳河两岸的头一抹绿色,为朗朗晴空泼上一笔颇具情调的重彩。酷似秦观的《如梦令·春景》:“依旧,依旧,人与绿杨俱瘦。”又像欧阳修的《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看来,古人总把春天与杨花柳絮,紧紧地绑在一起。其实,西方文人依旧多情,比如,俄国作家屠格涅夫曾在《孤狼》中写道:“放眼望去,一条很长的灰色雨云,正铺天盖地地迎面压来。爆竹柳好似受到惊吓一样摇曳不停,发出声声哀怨。闷热的天气顿时变得湿冷湿冷的,周围也昏暗起来。”总以为,俄国作家多半运笔沉重,想不到,北半球的疾风暴雨,还是袭击了摇曳不停地“爆竹柳”,想必这种描述,的确属于情景交融了吧。
其实,俄国的“爆竹柳”也好,欧阳修的“杨柳堆烟”也罢,彼此之间,各有各的思维与情趣。毕竟,滏阳河两岸的春风,最早唤醒的,反倒是随风而动的柳丝依依吧。柳絮如烟,朵朵嫩白的绒线团,悄然抛向茫茫四野与浩瀚长空。微风缓拂,面颊敏感,每颗心都柔柔的、痒痒的。
忽然想起,丰子恺先生的散文名篇《杨柳》,他特意写道:“听人说,这种植物是最贱的。剪一根枝条来插在地上,它也会活起来,后来,变成一株大杨柳树。它不需要高贵的肥料或工深的壅培,只要有阳光、泥土和水,便会生活,而且生得非常强健而美丽。”
难怪林语堂引证李渔谈论柳树的名言:“柳贵乎垂,不垂则可无柳。柳条贵长,不长则无袅娜之致,徒垂无益也。此树为纳蝉之所,诸鸟亦集。长夏不寂寞,得时闻鼓吹者,是树皆有功,而高柳为最。”能把春心萌动的柳树,与世间的人生哲理归拢到一起,正应了林语堂苦思冥想的主题——生活的乐趣。
初春,冀中池塘,冰消波起,柳绿鸭嬉。循着泛绿的小路觅柳而行,一排排杨柳朦朦胧胧,弥漫起一树黄雾,飘逸出春天的芬芳。绿得是那么淡雅、清爽、生动,排列组合成春天的韵律。滏阳水盛,尤其在柳丝飘飞之后的日子里,货艇、渔船,可以顺着一路清风,赶到石桥左右的街巷,卸货、载酒、囤果与贩鲜……老家盛产玉米高粱、瓜果梨桃,有的是滏阳河畔的酒坊茶肆,老白干的醇厚浓香,醉了中国几百年。还用问吗?借着初春杨柳绿、岸边水酒鲜,湖边河畔的生活梦想,早就一代一代地繁衍开来。
春天就这么多情多义。不知不觉间,迎春花开,嫩柳初绿,热热闹闹的生活,悄然抵达了崭新的方向。显然,丰子恺先生细腻敏感,在他心目中,“别的树木都凭仗了东君的势力而拼命向上,一味好高,忘记了自己的根本,其贪婪之相不合于春的精神。最能象征春的神意的,只有垂杨。”殊不知,无论丰子恺老家江浙坊间,还是冀中滏阳两岸,垂杨嫩柳也好,牡丹梅花也罢,这些花草树木的灵魂,早已细密地缠绕在一起,绝非几首多情的诗、几段妙曼的词,就能轻易俘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