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大
- 缩小
- 默认
伟大也要有人懂
——再读《人类的群星闪耀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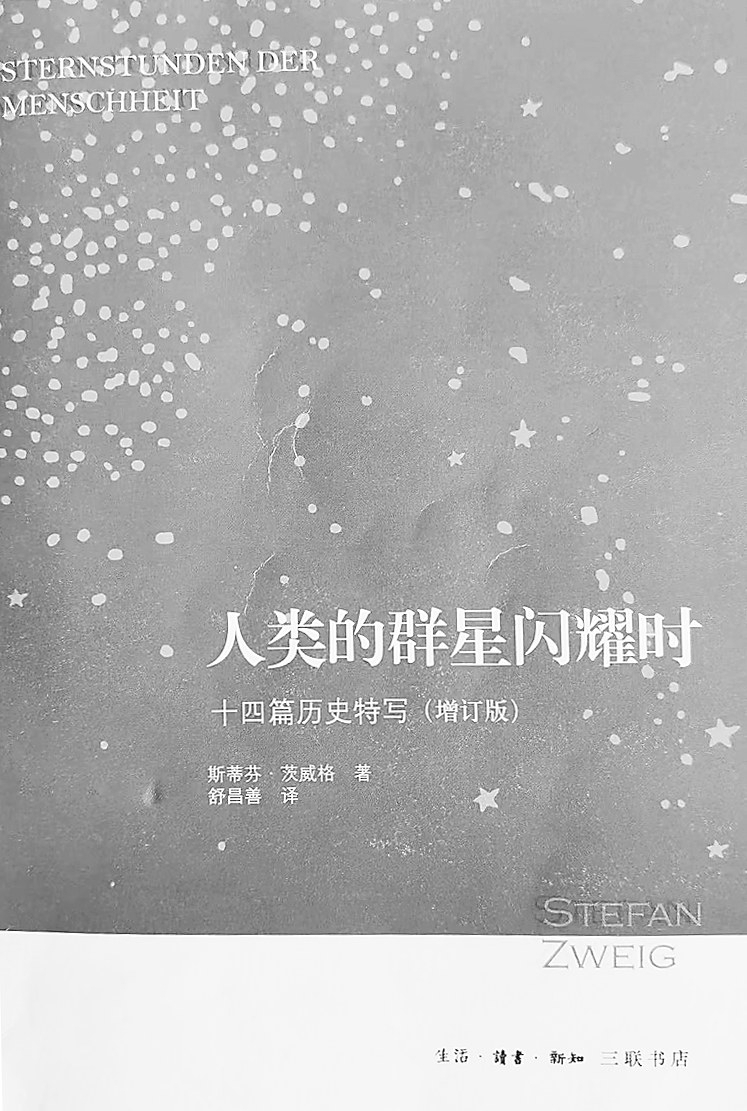
李增军
“在一个民族内部,为了产生一位天才,总是需要几百万人。一个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刻出现以前,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无谓地流失。”
这是斯蒂芬·茨威格在《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序言里写的一段话。在这本书里,他用十四个历史故事讲述了十四个创造和决定历史的时刻,包括太平洋的发现、拜占庭的陷落、拿破仑的滑铁卢战役、列宁的十月革命、《弥赛亚》的创作、《马赛曲》的诞生、歌德的《玛丽恩巴德悲歌》、黄金国的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刑场瞬间、越过大洋的第一条海底电缆、离家出走的托尔斯泰、人类第一次南极探险、守望共和的西塞罗之死以及威尔逊的梦想和失败。
茨威格把这些故事定位为历史特写。他说:“我丝毫不想通过自己的虚构来增加或冲淡所发生的一切的内外真实性,因为历史本身在那些非常时刻已表现得十分完全,无须任何后来的帮手。历史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一个作家都别想超越历史本身。”虽然是历史特写,不是历史传奇或历史小说,但茨威格在书写历史时的激情和浪漫,让我每每读起的时候都像听一场音乐会,高潮迭起、激情澎湃!不,不是高潮迭起!余华说得更准确:茨威格上来就给我叙述的高潮,而且这个高潮持续到最后!
历史人物无疑都是天才。他们不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在关键的时刻会决定历史的走向。茨威格笔下的历史人物,不是高在天上,而就在人群当中,在他们身上既闪耀着伟大人物的人性光辉,也有普通人身上的世故和懦弱,甚至会有人性中令人不齿的恶。巴尔沃亚在发现“南边的大海”(太平洋)的前夜,用惨无人道的残酷玷污了自己的名声:他将一批失去反抗能力的印第安人俘虏缚住手脚让一群饥饿的狼狗撕咬、吞吃,在他名垂青史的同时也使他遗臭万年。奥斯曼帝国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在1453年5月29日攻占了拜占庭,标志着东罗马帝国的灭亡,欧洲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然而,也是在胜利的前夜,他向士兵许下了可怕的誓言:在攻克拜占庭城以后允许部队官兵尽情劫掠三天,家什器具、金钱珠宝、男人女人和孩子,所有一切都属于打了胜仗的士兵,而他本人将放弃所有这些东西,他只要征服东罗马帝国这个最后堡垒的荣誉。他完全兑现了承诺,甚至圣索菲亚大教堂也没有幸免于难。攻占拜占庭给他带来无尚的荣誉,也给他带来难以磨灭的耻辱。在茨威格笔下,古罗马政治家、思想家西塞罗作为共和政体的捍卫者被专制独裁者杀害时的悲情,美国总统威尔逊追求人类永久和平的政治理想遭遇旧欧洲道德堕落抵制时的落寞,亨德尔创作《弥撒亚》时带来的肉体和精神的复活,以及年迈的歌德接受年轻的乌尔丽克拥吻令他难以忘怀的心情激荡,都是那么鲜活生动。
历史发展有它自身的逻辑。我们更多关注群星闪耀,关注高光时刻,但高光和群星背后是漫长岁月等待和前赴后继的探索。历史事件都有偶然性,但偶然性背后有必然性和确定性。奥斯曼帝国虽然强大,穆罕默德二世带领部队围攻一个多月,特制大炮在外城墙上轰炸了无数个大洞,仍然对攻进拜占庭城去束手无策。如果不是那扇供行人通过的小城门,如果这扇小城门没有被东罗马士兵忘记,如果土耳其禁卫军没有发现这扇小门,那么,拜占庭的命运会不会改变?这扇叫凯尔卡门的城门改写了欧洲乃至世界的历史。但是,历史没有如果!拿破仑和威灵顿的部队的滑铁卢战役,我们看过无数次的描述,这次战役像一部扣人心弦的戏剧,一会儿陷入低谷,一会儿又充满希望,双方不断变换着有利位置。如果拿破仑不是重用了格鲁希,如果格鲁希的部队能够及时过来增援,固执又平庸的格鲁希一分钟的考虑改变了拿破仑和世界的命运。但是,历史没有如果!
也许,西塞罗、拿破仑这十四位历史人物应该感谢和茨威格的“遇见”。茨威格就像他们的知音,走进了他们的内心,走进了他们的故事,他不是一个旁观者,更像一个亲历者。维茨格让他们从伟大走向平凡,又从平凡走向不朽。那么,他们之间的“遇见”呢?是偶然,是必然,还是偶然之中的必然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