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大
- 缩小
- 默认
怀念一头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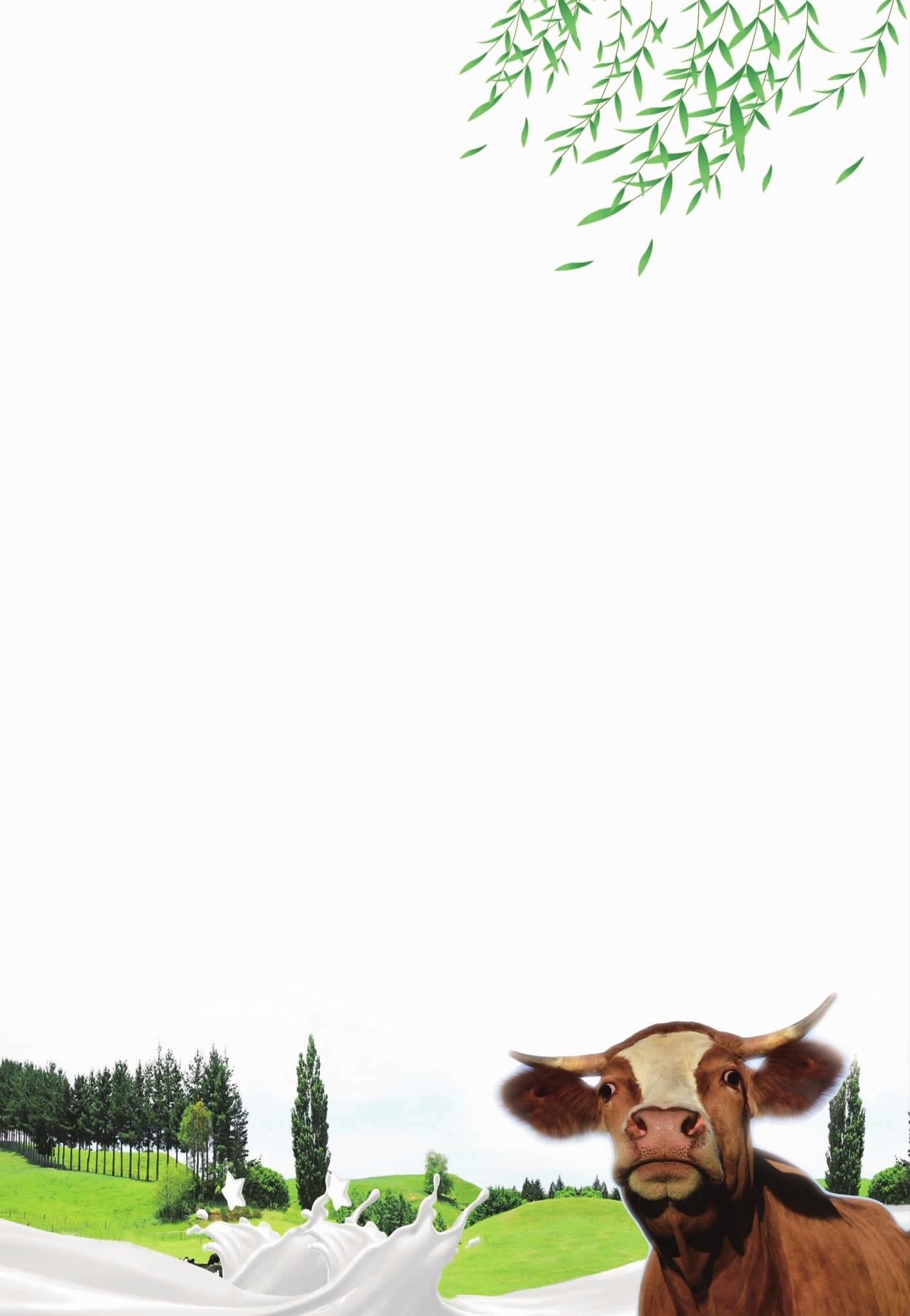
文/丁够生
“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虽无短笛,我,曾经就是一位牧童,俗称放牛娃,六七岁就开始放牛。有一头母黄牛,从小由我喂养大,一放就是十多年,至今历历在目。
那头黄牛,浑身长着一身黄褐色的毛,毛色光亮,就像披了一身黄绸缎。四个蹄子上方有一圈雪白的毛,就像带白色的脚环,听懂行的牛贩子说,这叫“四蹄踏雪”,这种牛可谓是牛中极品。鼻梁正上方灰黑色,牛角像只刚出土的小竹笋,双眸炯炯有神,给人聪明温顺的感觉。也正因如此,父母放心地打小就把它交给了我喂养,我喜欢得不得了,还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小黄。
在农村,放牛是个轻松活。哥哥姐姐往往跟大人去田里插秧、收割,或者上山打柴,或者到菜地摘辣椒、收花生等。作为老幺,我自然就是放放牛。但养牛其实也不容易,一年四季都得喂,几乎早晚都要去放。放牛,自然占据了我不少童年时光。小黄,俨然也是我童年,乃至青少年时代的亲密伙伴,在我的心里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多少个清晨,我迎着朝霞,牵着小黄在绿油油的田埂边吃草;多少个傍晚,我牵着小黄伴着夕阳回家。有时为了让小黄吃到更肥的草,跑得比较远,回来太晚还要穿过黑黝黝的山野,甚至路旁还有坟地。因为听过村里老人讲过不少鬼故事,往往也是汗毛倒竖,只好扬着鞭子吓唬小黄快速穿过。不管如何,一路上还有小黄作伴,心里多少踏实了几分。
一般来说,早晨时间短,加上要上学,不敢走远,往往就在村子旁边放牛,牛儿往往吃不饱,因此,放牛的最佳时间是下午,一般要放好几个小时,牛儿吃得肚子鼓鼓的才回家。看牛吃草,有时也会感觉很乏味,尤其是没有和小伙伴一块去放牛的时候,我常常会带本书或杂志去看。那时,书和杂志都是农村的“奢侈品”,我家是很少有这个闲钱去买的,因此多半是找别人家借阅。记得借得多的是《山海经》《故事会》《杜鹃花》之类的书刊,偶尔还有一些儿童连环画。那时的我,对书刊如饥似渴,如饮甘霖,几乎把村里能借到的书刊都借来了,甚至村里订的《农村百事通》杂志,我也几乎每期不落地看。小学时代,我的成绩特别好,尤其作文写得不错,每每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念给全班听,我想这与我在放牛的时候,大量阅读各种书刊有关。放牛还带书刊去看,在小伙伴当中有点另类,却被很多村民传为美谈,每每受到村民表扬,我心里便乐滋滋的。
山野牧牛心自静,世间喧闹不闻听。确实也有因看书太投入,而让牛走失的时候。有时,为了偷懒,就把牛赶到山上去吃草,把牛绳绑在牛角上,把它扔到没有高大树木的小山窝里,任由它吃各种草或嫩竹叶。边看书边时不时看看牛在哪,有时看得太入迷了,回过神来再去找小黄,却不见了,于是慌慌张张到处寻找。有时找不着,只好垂头丧气回家,却惊喜地发现聪明的牛儿已经自己回家了。但偶尔也会有牛跑到别人家的田地里偷吃或踩坏庄稼的现象。农村人视庄稼如命,因此也曾被人家气汹汹地上门告状,赔了人家庄稼不说,自然也少不了一顿挨骂,甚至挨打。这个时候,往往对小黄恨得直咬牙。
当然,小黄总体来说,就像我们山里人,踏实肯干、憨厚朴实,很少惹祸。有时,还仿佛很通人性。比如,在田埂上牵它吃草的时候,它几乎从不偷吃庄稼,哪怕这个禾苗很鲜嫩,哪怕田埂上没有多少肥草。又如,农忙时节,有时让它独自拉稻谷回家,它也能顺利完成使命,拉到家门口,静候主人回来收拾好。
记得在小黄还不到2岁的时候,在父亲的调教下,就学会了耕田、拉车、犁地,从此,家里的重活就全部落在小黄的身上。那时家里人口多,分了十多亩田,还有七八亩地,没有机械化,犁田耙地等重活全靠小黄。不管春耕还是盛夏的双抢,抑或是冬天种油菜,小黄凭着一股牛劲蛮力,负重前行。它的肩胛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扛着犁耙,渐渐磨出了厚厚的茧。那时,牛与人的亲切感情,或许出于农耕时代牛力的不可取代性。每个农村家庭,几乎都会把牛儿当作一位家庭成员来珍爱。我家小黄也不例外,每每牛没有吃饱的时候,父亲便会拿一些谷糠或者米饭给它加加餐,双抢时节,甚至还会直接给它加些酒糟、鸡蛋、盐,给它补充营养。
“牛背稳于舟,牧儿忘百忧。晚凉过溪去,落日在林头。”这是明朝诗人胡奎在《题牛》中描绘的一副牧童骑牛的美好场景。但凡牧童,往往也会去骑牛玩玩。小黄对骑它的人很排斥,一骑就会跑动,吓得别人都不敢靠近,但对我却是一个例外。有时候放牛回家,我也会骑着它玩一会儿,左手挽住牛绳,右手紧紧抓住牛背,脚用力一蹬就稳稳地坐在牛背上了。要想走快点,便用右手拍打一下牛屁股,或者两腿一夹紧,小黄就会走快一点,要走慢一点,左手扯住一下牛绳就好。但出于爱惜小黄,我舍不得骑它,因此很少骑。
小黄最大的贡献,莫过于每年给我们家产下一头小牛犊。当小黄长到2岁半的时候,就给我们家产下了第一头公的小牛犊,生下来很快就会走路吃奶,也不怕人,正应了那句“初生牛犊不怕虎”。倒是小黄比较紧张,生怕别人动了它的宝宝,还时不时去舔一下小牛犊的皮毛,一副爱子情深的样子。大概喂养了不到一年,小牛犊就被牛贩子上门收购走了,从此我们家每年多了好几百元的收入。在20世纪80年代,几百元可是能解决不少家庭开支的,我们兄弟姐妹的学杂费、生活费等开销,往往就靠这笔收入。因此,我们都对小黄珍爱有加,它确实是我们家的“摇钱树”。
当时,关牛的地方是村集体统一盖的牛棚,后来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分给了农户。因为二十多头牛关在一块,相互之间只是用了木栏隔开,因此牛棚里空气总是充斥着牛粪牛尿味,夏天的时候,蚊虫更是到处乱飞。为了改善牛的生活环境,我们几乎每天都会拿一块干稻草铺在牛窝里,聪明的小黄也往往固定在一个角落拉屎拉尿。父亲会时不时去清理,把它倒在一个空旷的地方,过上一段时间,便是上等的农家肥,挑到田里或地里。有时,我也会发现小黄身上还会长一些蜱虫,吸牛的血,有时吃得圆鼓鼓的。对这种寄生虫,我自然恨之入骨,发现了,便会把它抓下来,然后用石头把它们砸死。看着血淋淋的蜱虫尸体,我会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每每帮小黄抓蜱虫的时候,它也似乎很感激,时不时地用眼睛瞅瞅我。有时,它甚至会伸出舌头来舔舔我的手,尾巴快活地左右摇摆,仿佛在感谢我。
小黄接连为我们家生了十几头牛犊,为了改善家庭经济条件,都被卖掉了,至今全家都感恩它的好,可谓是我家的大功臣。后来,我上了高中,离家乡也越来越远了,放牛的次数也屈指可数了。有一次回家,却发现小黄不见了,我急忙去问母亲,母亲告诉我小黄已经卖掉了。瞬间,我的眼泪就掉了下来。我问母亲,为什么要卖掉呀?母亲也抹眼泪,无奈地说,家中经济比较紧,又要供你们兄弟俩上学,小黄老了,活也干不动了,已经几年不生崽了,只好卖掉了。
也许,这终究是牛的宿命。于一个贫寒的家庭而言,不忍心自己宰杀,卖掉也是一个无奈的选择。但,小黄,一头勤劳的牛,懂事的牛,曾经陪伴我走过一年四季,曾经陪伴了我的童年、少年,就像一位家人,一块同甘共苦,一起守望家园。在放牛的那么漫长的时光,我经常静静看书,静静思考,品味人生。我应该感谢我的小黄,它教会了我勤劳,让我懂得了坚韧,让我领悟到了“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的道理,也坚定了我走出大山,去为理想而奋斗的决心。
我不知道小黄最终的下落与命运,但我永远感恩它对我们家的付出,永远怀念这位亲密的好朋友,也将永远激励自己成为拥有“老黄牛”精神的人:吃苦耐劳、坚韧善良、锲而不舍、乐于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