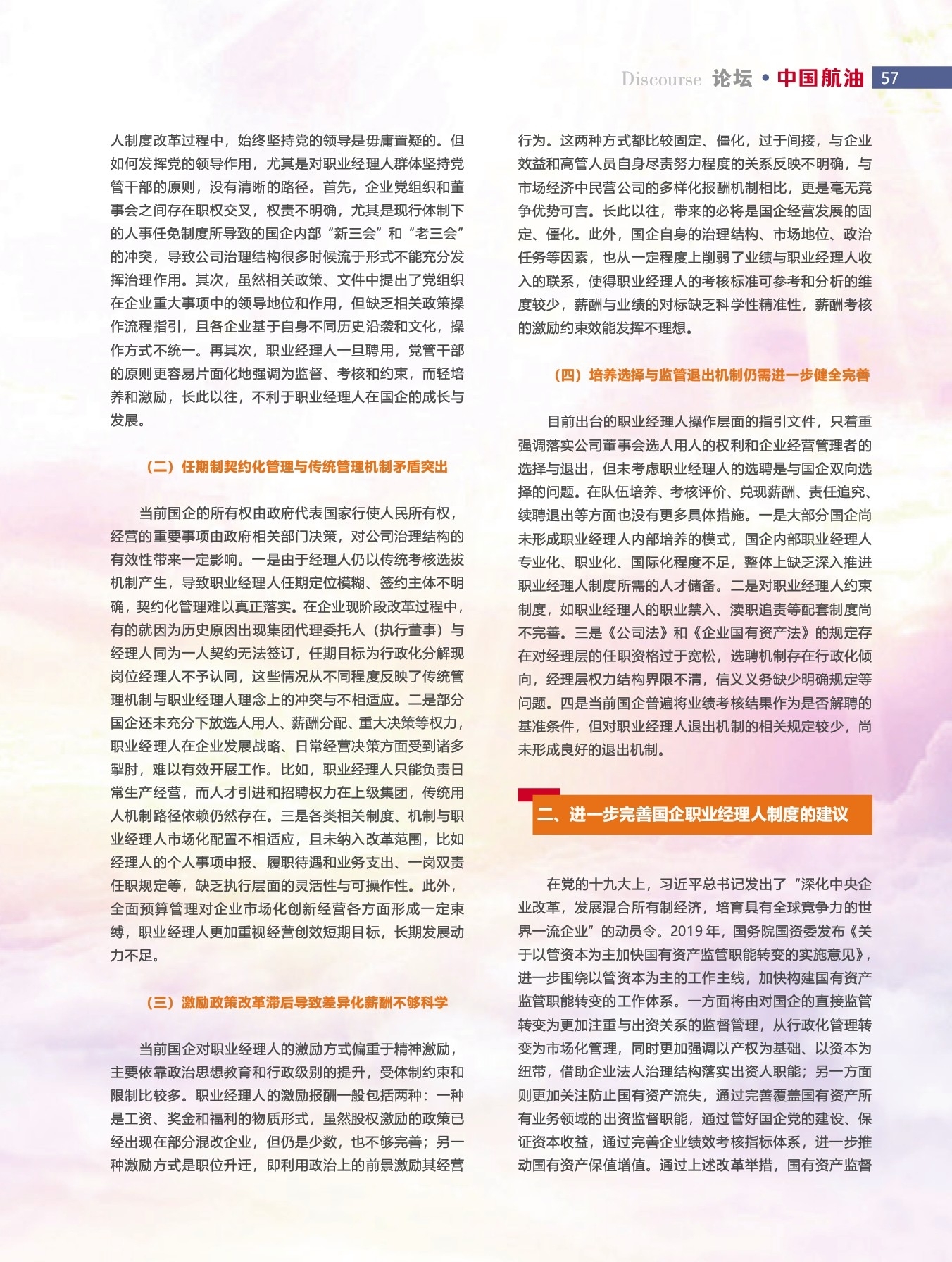- 放大
- 缩小
- 默认
国企职业经理人制度实践与启示
人制度改革过程中,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是毋庸置疑的。但如何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尤其是对职业经理人群体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没有清晰的路径。首先,企业党组织和董事会之间存在职权交叉,权责不明确,尤其是现行体制下的人事任免制度所导致的国企内部“新三会”和“老三会”的冲突,导致公司治理结构很多时候流于形式不能充分发挥治理作用。其次,虽然相关政策、文件中提出了党组织在企业重大事项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但缺乏相关政策操作流程指引,且各企业基于自身不同历史沿袭和文化,操作方式不统一。再其次,职业经理人一旦聘用,党管干部的原则更容易片面化地强调为监督、考核和约束,而轻培养和激励,长此以往,不利于职业经理人在国企的成长与发展。
(二)任期制契约化管理与传统管理机制矛盾突出
当前国企的所有权由政府代表国家行使人民所有权,经营的重要事项由政府相关部门决策,对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性带来一定影响。一是由于经理人仍以传统考核选拔机制产生,导致职业经理人任期定位模糊、签约主体不明确,契约化管理难以真正落实。在企业现阶段改革过程中,有的就因为历史原因出现集团代理委托人(执行董事)与经理人同为一人契约无法签订,任期目标为行政化分解现岗位经理人不予认同,这些情况从不同程度反映了传统管理机制与职业经理人理念上的冲突与不相适应。二是部分国企还未充分下放选人用人、薪酬分配、重大决策等权力,职业经理人在企业发展战略、日常经营决策方面受到诸多掣肘,难以有效开展工作。比如,职业经理人只能负责日常生产经营,而人才引进和招聘权力在上级集团,传统用人机制路径依赖仍然存在。三是各类相关制度、机制与职业经理人市场化配置不相适应,且未纳入改革范围,比如经理人的个人事项申报、履职待遇和业务支出、一岗双责任职规定等,缺乏执行层面的灵活性与可操作性。此外,全面预算管理对企业市场化创新经营各方面形成一定束缚,职业经理人更加重视经营创效短期目标,长期发展动力不足。
(三)激励政策改革滞后导致差异化薪酬不够科学
当前国企对职业经理人的激励方式偏重于精神激励,主要依靠政治思想教育和行政级别的提升,受体制约束和限制比较多。职业经理人的激励报酬一般包括两种:一种是工资、奖金和福利的物质形式,虽然股权激励的政策已经出现在部分混改企业,但仍是少数,也不够完善;另一种激励方式是职位升迁,即利用政治上的前景激励其经营行为。这两种方式都比较固定、僵化,过于间接,与企业效益和高管人员自身尽责努力程度的关系反映不明确,与市场经济中民营公司的多样化报酬机制相比,更是毫无竞争优势可言。长此以往,带来的必将是国企经营发展的固定、僵化。此外,国企自身的治理结构、市场地位、政治任务等因素,也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业绩与职业经理人收入的联系,使得职业经理人的考核标准可参考和分析的维度较少,薪酬与业绩的对标缺乏科学性精准性,薪酬考核的激励约束效能发挥不理想。
(四)培养选择与监管退出机制仍需进一步健全完善
目前出台的职业经理人操作层面的指引文件,只着重强调落实公司董事会选人用人的权利和企业经营管理者的选择与退出,但未考虑职业经理人的选聘是与国企双向选择的问题。在队伍培养、考核评价、兑现薪酬、责任追究、续聘退出等方面也没有更多具体措施。一是大部分国企尚未形成职业经理人内部培养的模式,国企内部职业经理人专业化、职业化、国际化程度不足,整体上缺乏深入推进职业经理人制度所需的人才储备。二是对职业经理人约束制度,如职业经理人的职业禁入、渎职追责等配套制度尚不完善。三是《公司法》和《企业国有资产法》的规定存在对经理层的任职资格过于宽松,选聘机制存在行政化倾向,经理层权力结构界限不清,信义义务缺少明确规定等问题。四是当前国企普遍将业绩考核结果作为是否解聘的基准条件,但对职业经理人退出机制的相关规定较少,尚未形成良好的退出机制。
二、进一步完善国企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建议
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了“深化中央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动员令。2019年,国务院国资委发布《关于以管资本为主加快国有资产监管职能转变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围绕以管资本为主的工作主线,加快构建国有资产监管职能转变的工作体系。一方面将由对国企的直接监管转变为更加注重与出资关系的监督管理,从行政化管理转变为市场化管理,同时更加强调以产权为基础、以资本为纽带,借助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落实出资人职能;另一方面则更加关注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通过完善覆盖国有资产所有业务领域的出资监督职能,通过管好国企党的建设、保证资本收益,通过完善企业绩效考核指标体系,进一步推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通过上述改革举措,国有资产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