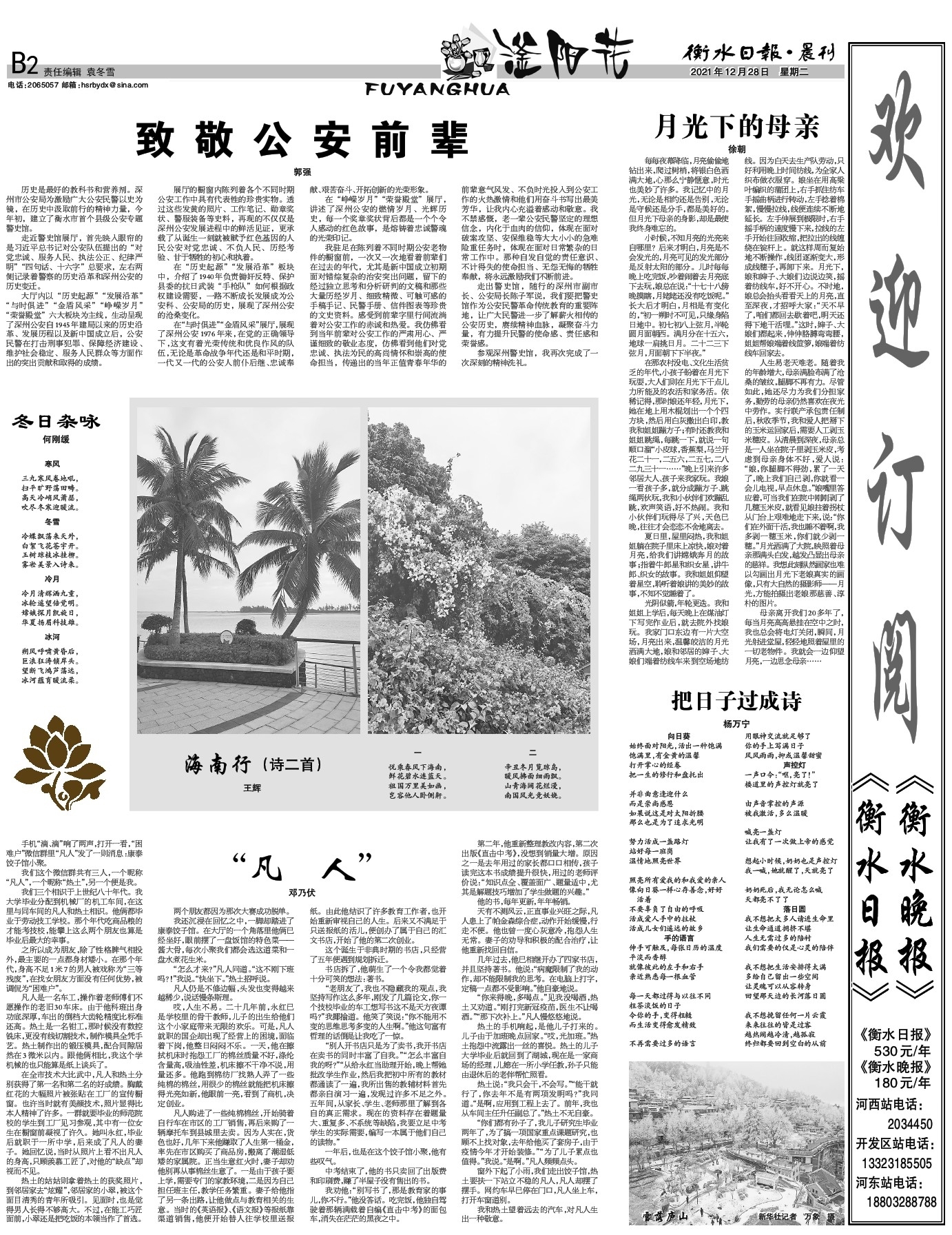月光下的母亲
徐朝
每每夜幕降临,月亮偷偷地钻出来,爬过树梢,将银白色洒满大地,心那么宁静惬意,时光也美妙了许多。我记忆中的月光,无论是相约还是告别,无论是守候还是分手,都是美好的。但月光下母亲的身影,却是最使我终身难忘的。
小时候,不知月亮的光亮来自哪里?后来才明白,月亮是不会发光的,月亮可见的发光部分是反射太阳的部分。儿时每每晚上吃完饭,吵着闹着去月亮底下去玩,娘总在说:“十七十八傍晚摸瞎,月姥姥还没有吃饭呢。”长大后才明白,月相是有变化的,“初一朔时不可见,只缘身陷日地中。初七初八上弦月,半轮圆月面朝西。满月分在十五六,地球一肩挑日月。二十二三下弦月,月面朝下下半夜。”
在那农村没电、文化生活贫乏的年代,小孩子盼着在月光下玩耍,大人们则在月光下干点儿力所能及的农活和家务活。依稀记得,那时娘还年轻,月光下,她在地上用木棍划出一个个四方块,然后用白灰撒出白印,教我和姐姐蹦方子;有时还教我和姐姐跳绳,每跳一下,就说一句顺口溜“小皮球,香蕉梨,马兰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晚上引来许多邻居大人、孩子来我家玩。我娘一看孩子多,就分成蹦方子、跳绳两伙玩,我和小伙伴们欢蹦乱跳,欢声笑语,好不热闹。我和小伙伴们玩得尽了兴,天色已晚,往往才会恋恋不舍地离去。
夏日里,屋里闷热,我和姐姐躺在院子里床上凉快,娘对着月亮,给我们讲嫦娥奔月的故事;指着牛郎星和织女星,讲牛郎、织女的故事。我和姐姐仰望着星空,聆听着娘讲的美妙的故事,不知不觉睡着了。
光阴似箭,年轮更迭。我和姐姐上学后,每天晚上在煤油灯下写完作业后,就去院外找娘玩。我家门口东边有一片大空场,月亮出来,温馨皎洁的月光洒满大地,娘和邻居的婶子、大娘们端着纺线车来到空场地纺线。因为白天去生产队劳动,只好利用晚上时间纺线,为全家人织布做衣服穿。娘坐在用高粱叶编织的蒲团上,右手抓住纺车手摇曲柄进行转动,左手捻着棉絮,慢慢拉线,线便连续不断地延长。左手伸展到极限时,右手摇手柄的速度慢下来,拉线的左手开始往回收缩,把拉出的线缠绕在锭杆上。就这样周而复始地不断操作,线团逐渐变大,形成线穗子,再卸下来。月光下,娘和婶子、大娘们边说边笑,摇着纺线车,好不开心。不时地,娘总会抬头看看天上的月亮,直至深夜,才招呼大家:“天不早了,咱们都回去歇着吧,明天还得下地干活哩。”这时,婶子、大娘们都起来,伸伸胳膊弯弯腰,姐姐帮娘端着线笸箩,娘端着纺线车回家去。
人生易老天难老。随着我的年龄增大,母亲满脸布满了沧桑的皱纹,腿脚不再有力。尽管如此,她还尽力为我们分担家务,勤劳的母亲仍然喜欢在夜光中劳作。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秋收季节,我和爱人把掰下的玉米运回家后,需要人工剥玉米穗皮。从清晨到深夜,母亲总是一人坐在院子里剥玉米皮,考虑到母亲身体不好,爱人说:“娘,你腿脚不得劲,累了一天了,晚上我们自己剥,你就看一会儿电视,早点休息。”娘嘴里答应着,可当我们在院中刚刚剥了几穗玉米皮,就看见娘拄着拐杖从门台上艰难地走下来,说:“你们在外面干活,我也睡不着啊,我多剥一穗玉米,你们就少剥一穗。”月光洒满了大院,映照着母亲那满头白发,越发凸显出母亲的慈祥。我想此刻纵然画家也难以勾画出月光下老娘真实的画像,只有大自然的摄影师——月光,方能拍摄出老娘那慈善、淳朴的图片。
母亲离开我们20多年了,每当月亮高高悬挂在空中之时,我也总会将电灯关闭,瞬间,月光射进堂屋,轻轻地照着屋里的一切老物件。我就会一边仰望月亮,一边思念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