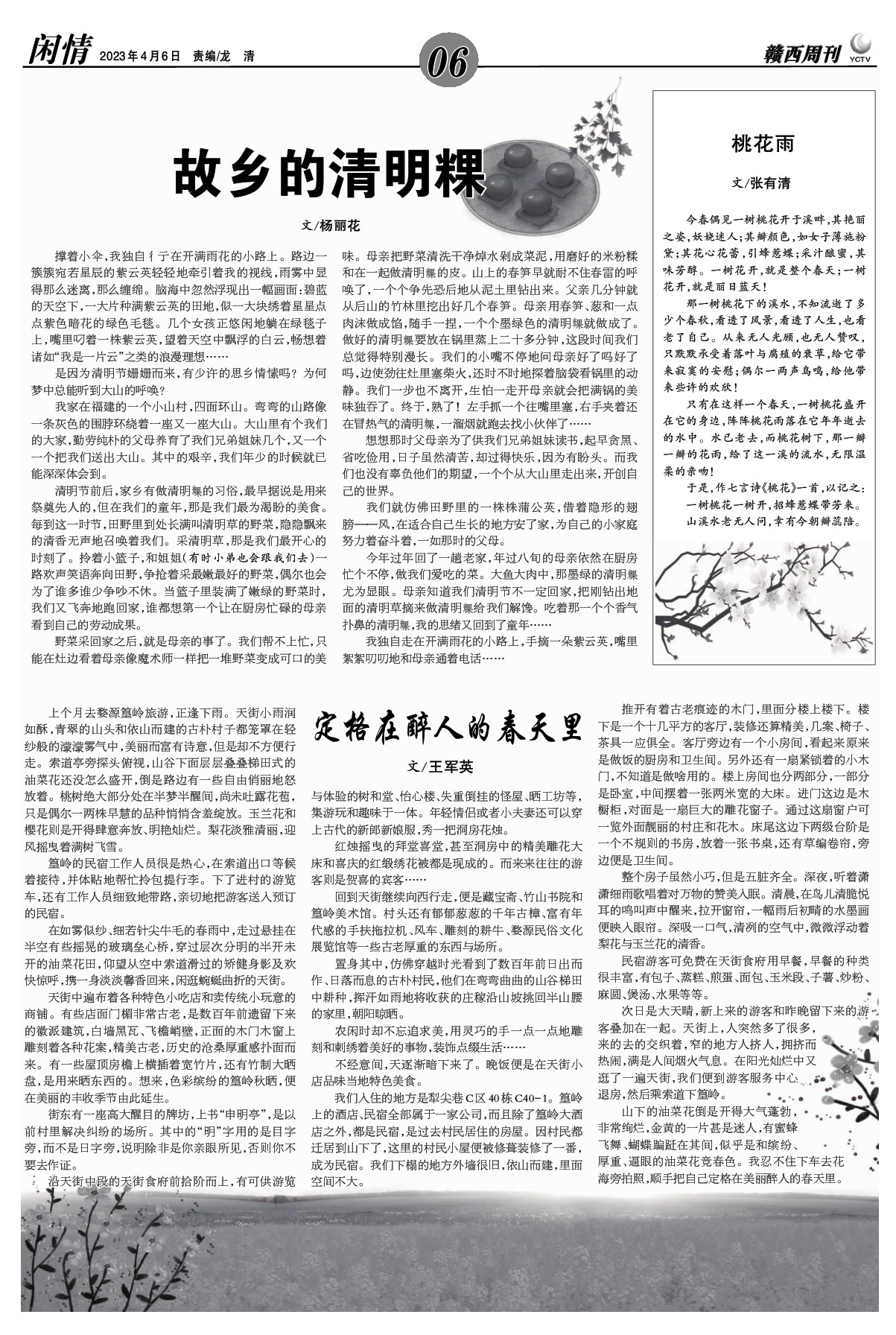- 放大
- 缩小
- 默认
故乡的清明粿

文/杨丽花
撑着小伞,我独自彳亍在开满雨花的小路上。路边一簇簇宛若星辰的紫云英轻轻地牵引着我的视线,雨雾中显得那么迷离,那么缠绵。脑海中忽然浮现出一幅画面:碧蓝的天空下,一大片种满紫云英的田地,似一大块绣着星星点点紫色暗花的绿色毛毯。几个女孩正悠闲地躺在绿毯子上,嘴里叼着一株紫云英,望着天空中飘浮的白云,畅想着诸如“我是一片云”之类的浪漫理想……
是因为清明节姗姗而来,有少许的思乡情愫吗?为何梦中总能听到大山的呼唤?
我家在福建的一个小山村,四面环山。弯弯的山路像一条灰色的围脖环绕着一座又一座大山。大山里有个我们的大家,勤劳纯朴的父母养育了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又一个一个把我们送出大山。其中的艰辛,我们年少的时候就已能深深体会到。
清明节前后,家乡有做清明粿的习俗,最早据说是用来祭奠先人的,但在我们的童年,那是我们最为渴盼的美食。每到这一时节,田野里到处长满叫清明草的野菜,隐隐飘来的清香无声地召唤着我们。采清明草,那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刻了。拎着小篮子,和姐姐(有时小弟也会跟我们去)一路欢声笑语奔向田野,争抢着采最嫩最好的野菜,偶尔也会为了谁多谁少争吵不休。当篮子里装满了嫩绿的野菜时,我们又飞奔地跑回家,谁都想第一个让在厨房忙碌的母亲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
野菜采回家之后,就是母亲的事了。我们帮不上忙,只能在灶边看着母亲像魔术师一样把一堆野菜变成可口的美味。母亲把野菜清洗干净焯水剁成菜泥,用磨好的米粉糅和在一起做清明粿的皮。山上的春笋早就耐不住春雷的呼唤了,一个个争先恐后地从泥土里钻出来。父亲几分钟就从后山的竹林里挖出好几个春笋。母亲用春笋、葱和一点肉沫做成馅,随手一捏,一个个墨绿色的清明粿就做成了。做好的清明粿要放在锅里蒸上二十多分钟,这段时间我们总觉得特别漫长。我们的小嘴不停地问母亲好了吗好了吗,边使劲往灶里塞柴火,还时不时地探着脑袋看锅里的动静。我们一步也不离开,生怕一走开母亲就会把满锅的美味独吞了。终于,熟了!左手抓一个往嘴里塞,右手夹着还在冒热气的清明粿,一溜烟就跑去找小伙伴了……
想想那时父母亲为了供我们兄弟姐妹读书,起早贪黑、省吃俭用,日子虽然清苦,却过得快乐,因为有盼头。而我们也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一个个从大山里走出来,开创自己的世界。
我们就仿佛田野里的一株株蒲公英,借着隐形的翅膀——风,在适合自己生长的地方安了家,为自己的小家庭努力着奋斗着,一如那时的父母。
今年过年回了一趟老家,年过八旬的母亲依然在厨房忙个不停,做我们爱吃的菜。大鱼大肉中,那墨绿的清明粿尤为显眼。母亲知道我们清明节不一定回家,把刚钻出地面的清明草摘来做清明粿给我们解馋。吃着那一个个香气扑鼻的清明粿,我的思绪又回到了童年……
我独自走在开满雨花的小路上,手摘一朵紫云英,嘴里絮絮叨叨地和母亲通着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