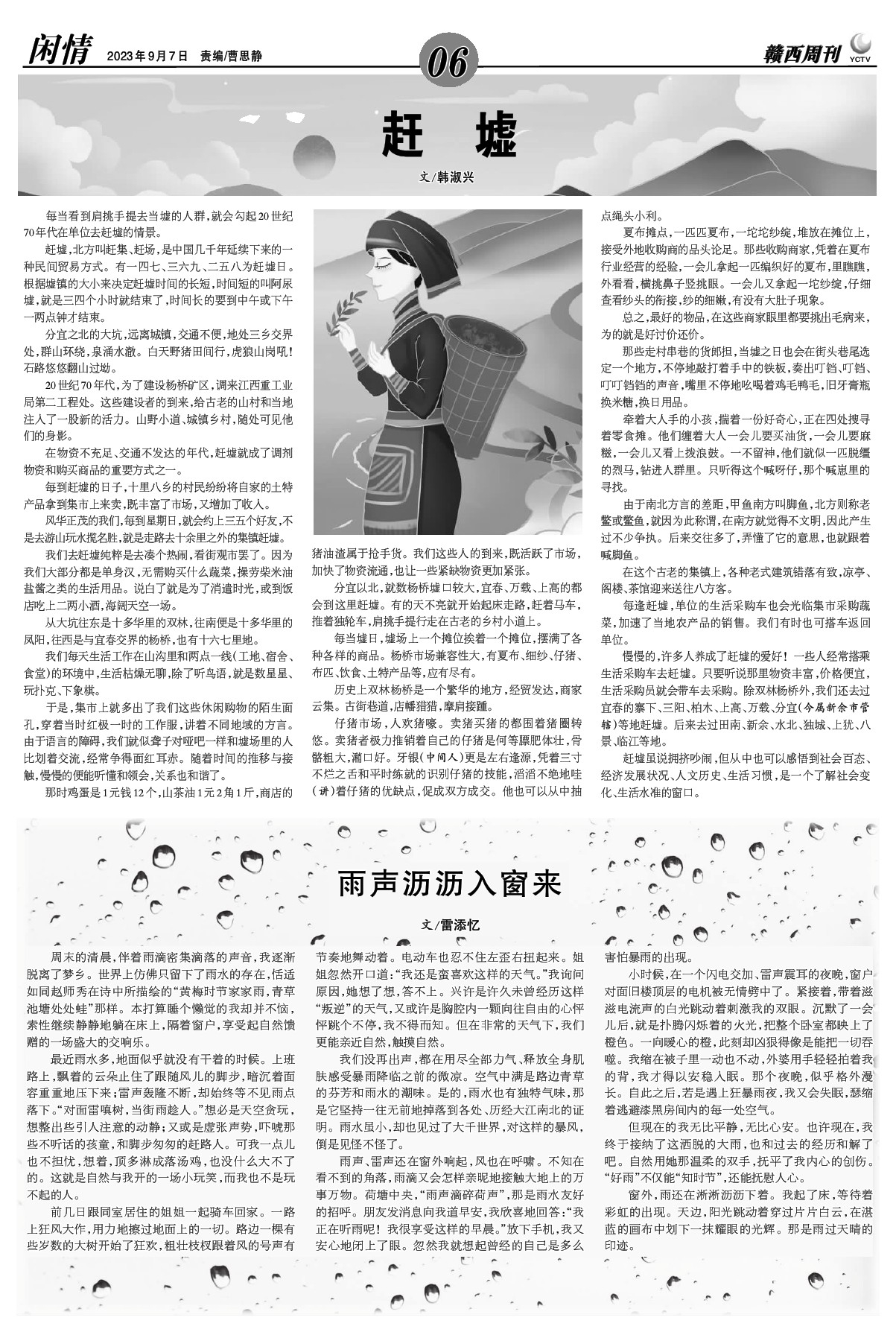- 放大
- 缩小
- 默认
赶墟

文/韩淑兴
每当看到肩挑手提去当墟的人群,就会勾起20世纪70年代在单位去赶墟的情景。
赶墟,北方叫赶集、赶场,是中国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一种民间贸易方式。有一四七、三六九、二五八为赶墟日。根据墟镇的大小来决定赶墟时间的长短,时间短的叫阿尿墟,就是三四个小时就结束了,时间长的要到中午或下午一两点钟才结束。
分宜之北的大坑,远离城镇,交通不便,地处三乡交界处,群山环绕,泉涌水澈。白天野猪田间行,虎狼山岗吼!石路悠悠翻山过坳。
20世纪70年代,为了建设杨桥矿区,调来江西重工业局第二工程处。这些建设者的到来,给古老的山村和当地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山野小道、城镇乡村,随处可见他们的身影。
在物资不充足、交通不发达的年代,赶墟就成了调剂物资和购买商品的重要方式之一。
每到赶墟的日子,十里八乡的村民纷纷将自家的土特产品拿到集市上来卖,既丰富了市场,又增加了收入。
风华正茂的我们,每到星期日,就会约上三五个好友,不是去游山玩水揽名胜,就是走路去十余里之外的集镇赶墟。
我们去赶墟纯粹是去凑个热闹,看街观市罢了。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单身汉,无需购买什么蔬菜,操劳柴米油盐酱之类的生活用品。说白了就是为了消遣时光,或到饭店吃上二两小酒,海阔天空一场。
从大坑往东是十多华里的双林,往南便是十多华里的凤阳,往西是与宜春交界的杨桥,也有十六七里地。
我们每天生活工作在山沟里和两点一线(工地、宿舍、食堂)的环境中,生活枯燥无聊,除了听鸟语,就是数星星、玩扑克、下象棋。
于是,集市上就多出了我们这些休闲购物的陌生面孔,穿着当时红极一时的工作服,讲着不同地域的方言。由于语言的障碍,我们就似聋子对哑吧一样和墟场里的人比划着交流,经常争得面红耳赤。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接触,慢慢的便能听懂和领会,关系也和谐了。
那时鸡蛋是1元钱12个,山茶油1元2角1斤,商店的猪油渣属于抢手货。我们这些人的到来,既活跃了市场,加快了物资流通,也让一些紧缺物资更加紧张。
分宜以北,就数杨桥墟口较大,宜春、万载、上高的都会到这里赶墟。有的天不亮就开始起床走路,赶着马车,推着独轮车,肩挑手提行走在古老的乡村小道上。
每当墟日,墟场上一个摊位挨着一个摊位,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商品。杨桥市场兼容性大,有夏布、细纱、仔猪、布匹、饮食、土特产品等,应有尽有。
历史上双林杨桥是一个繁华的地方,经贸发达,商家云集。古街巷道,店幡猎猎,摩肩接踵。
仔猪市场,人欢猪嚎。卖猪买猪的都围着猪圈转悠。卖猪者极力推销着自己的仔猪是何等膘肥体壮,骨骼粗大,潲口好。牙银(中间人)更是左右逢源,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和平时练就的识别仔猪的技能,滔滔不绝地哇(讲)着仔猪的优缺点,促成双方成交。他也可以从中抽点绳头小利。
夏布摊点,一匹匹夏布,一坨坨纱绽,堆放在摊位上,接受外地收购商的品头论足。那些收购商家,凭着在夏布行业经营的经验,一会儿拿起一匹编织好的夏布,里瞧瞧,外看看,横挑鼻子竖挑眼。一会儿又拿起一坨纱绽,仔细查看纱头的衔接,纱的细嫩,有没有大肚子现象。
总之,最好的物品,在这些商家眼里都要挑出毛病来,为的就是好讨价还价。
那些走村串巷的货郎担,当墟之日也会在街头巷尾选定一个地方,不停地敲打着手中的铁板,奏出叮铛、叮铛、叮叮铛铛的声音,嘴里不停地吆喝着鸡毛鸭毛,旧牙膏瓶换米糖,换日用品。
牵着大人手的小孩,揣着一份好奇心,正在四处搜寻着零食摊。他们缠着大人一会儿要买油货,一会儿要麻糍,一会儿又看上拨浪鼓。一不留神,他们就似一匹脱缰的烈马,钻进人群里。只听得这个喊呀仔,那个喊崽里的寻找。
由于南北方言的差距,甲鱼南方叫脚鱼,北方则称老鳖或鳖鱼,就因为此称谓,在南方就觉得不文明,因此产生过不少争执。后来交往多了,弄懂了它的意思,也就跟着喊脚鱼。
在这个古老的集镇上,各种老式建筑错落有致,凉亭、阁楼、茶馆迎来送往八方客。
每逢赶墟,单位的生活采购车也会光临集市采购蔬菜,加速了当地农产品的销售。我们有时也可搭车返回单位。
慢慢的,许多人养成了赶墟的爱好!一些人经常搭乘生活采购车去赶墟。只要听说那里物资丰富,价格便宜,生活采购员就会带车去采购。除双林杨桥外,我们还去过宜春的寨下、三阳、柏木、上高、万载、分宜(今属新余市管辖)等地赶墟。后来去过田南、新余、水北、独城、上犹、八景、临江等地。
赶墟虽说拥挤吵闹,但从中也可以感悟到社会百态、经济发展状况、人文历史、生活习惯,是一个了解社会变化、生活水准的窗口。